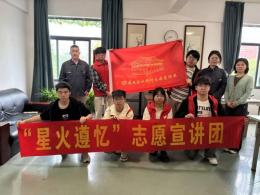孤月清寂,已经很安然地在夜幕里歇着了,我在辗转反侧间,听到了那个午后,我心里的答案:
“因为,我就是‘豆豆’。”
豆豆死后,很少再有科学家来南极考察时问一嘴“你每天都做什么”了,也很少会有企鹅回答“吃饭睡觉打豆豆了”,显而易见,他们怕,怕随波逐流被订上同流合污的标签,怕追责的火烧到每一位“旁观者”。中立者真的中立吗?“打豆豆”不过是一句口号的停用,浮出风平浪静水面下的,数以万计的“豆豆”。
我叫兜兜,是企鹅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与他们不同,我是主导者,掌握着主导权,我控制着场场狂欢的走向,自然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狂欢的中心,出事了有人兜着,我怕什么呢?豆豆是一个合格的弱者,不仅是因为它懦弱,同样的,它不一样,它是罕见的白化企鹅,但是不一样有时也会遭到排斥,理所应当的排斥。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而我恰恰喜欢这样“有缝的蛋”。“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它不懂,它太退让,可惜我喜欢的正是他的退让。它的不安,它的懦弱,都一步步导致了它的颤栗、它的屈辱、它的不堪。
学校会管吗?不尽然。一如湛江新闻里,教育部门敷衍搪塞的话语一样:“没有对女生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当时在嬉戏。”我用尖尖的喙去啄豆豆,有时是因为家庭原因心里不痛快,有时也只不过是为了嬉戏,好瞧见它连跌带爬的狼狈样儿。
“为什么只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多的声讨压着它,我不过只用得着轻飘飘一句“是它自己太敏感了吧”就能击垮它。我在弱者的沉默和示弱中血脉喷张,嗅到了血腥的快感。极具攻击性的锋利而扭曲的美,述说着我的恶意昭昭。我的耳畔充斥着精致利己者的一笑而过,它们附和或是袖手旁观,于是我在“掌声”中迷失,也在“鲜花”中遗忘。
我甚至忘了,在那个午后,我也是“豆豆”。
我也会痛苦无助,我也会被冠以“太脆弱”,也会哭,也会看到华丽地毯下的虱子,我开始反击,开始寻求安慰,直到我参透了自然的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如此而已。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我开始吃豆豆。
为什么呢,因为心里不平衡,需要一种心理补偿来宽慰自己,成为“豆豆”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极度缺乏安全感,也唯有同恶相济,开始模仿那些“打豆豆者”,去弱者身上寻求卓越感,才能填补我的内心。
在暴力得不到遏制的氛围下,所有人都两级分化成了豆豆和兜兜。
我是豆豆吗?还是兜兜?
我又想起了那个午后,科学家来到了南极,碰到了我们,科学家询问其中一只:“你每天都干什么呀?”,企鹅说:“吃饭、睡觉、打豆豆”,他问了很多企鹅,都是毫无例外的答案,后来,他碰到了一只小企鹅,也问同样的问题,小企鹅说:“吃饭、睡觉。”科学家问:“你为什么不打豆豆?”
小企鹅说:“因为我就是‘豆豆’。”
那只小企鹅就是我。
http://www.dxsbao.com/art/550055.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