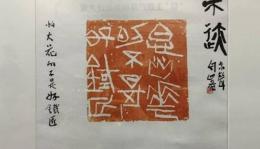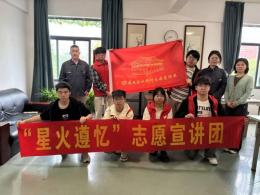威廉·福克纳是著名的美国作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其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以哥特式的恐怖元素,扭曲的人物心理,以及高超的叙事手法等闻名于世。《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讲述了在杰弗逊小镇上,南方没落贵族小姐艾米丽在式微的旧南方制度和父权制度的控制下,产生极度孤独、与社会疏离等一系列的创伤症状,最终选择用死亡来逃离这个悲剧人生。以往学者对《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创伤解读主要聚焦于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成因。个人从创伤理论出发,认为小说更多是传达了由冷漠无情的社会环境及腐朽的制度给艾米丽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心理创伤,百般无果的努力使她的悲剧人生成为必然。
“创伤理论”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精神病理学的歇斯底里症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师彦灵,2001)。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对“创伤”下过这样的定义:“如果在短暂的时期内,某个经验使心灵受到极其高度的刺激,致使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去适应,从而使其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故而可以说创伤是对受害者产生的无法抹去的身心痕迹。受创者在承受值降至一定程度时,往往会采取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求得救赎。文学上这种悲剧性的结尾常常成为解决创伤的唯一途径。朱迪斯•赫尔曼曾提过,创伤后应激反应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记忆侵扰,禁闭畏缩。我们目前在文学上所见的悲剧性结局,大概就属于以上类型应激之后的结果。创伤理论视角下对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分析如下:
一
小说中,艾米丽虽然一直生活在小镇上,却一直处于边缘化,“她就这样度过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这么多年也没跟镇上的人交往,但同时她“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她的存在被赋予了闪耀的光环,矛盾却让她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能一直活在束缚和禁锢中,最终放弃自我,成为性格孤僻怪异的透明人。除外,当代表团与艾米丽交流时,她没说几句话就将代表团成员赶出门外,也显示出她与整个社会深深的疏离感。
在艾米丽父亲死后,其行为上更是明显表现出被创伤压垮的症状,“她依然如平时一般打扮,脸上毫无哀恸之色。她对大家说,她的父亲并未辞世,一连三天,如是重复。”这里可以看出,此时艾米丽整个人已经处于麻木的状态。当被告知父亲的尸体必须埋葬时,她“垮下来了”,深知最后一棵稻草也不在了。之后艾米丽与巴伦的相遇让她重新点燃希望,但巴伦“无意成家”,这让艾米丽再次遭受创伤,从而陷入孤独苦寂中。艾米丽不顾一切追求的爱情,到头来竟是一场梦。因此,她买下砒霜,结束了爱人的生命。此后艾米丽家的前门“再也没打开过,只有她四十开外时,大约有六七年时间前门开过。”以上种种,都深刻地体现出了艾米丽孤独疏离的创伤症状。
二
艾米丽遭受创伤后的应激反应主要是过度警觉和禁闭畏缩。造成这些表现的原因主要来源于父亲的强权和当时没落的南方腐朽的社会环境,这些过往对她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艾米丽的创伤来源于家庭。弗洛伊德认为,在儿童发育期间,控制和释放能量的心理功能相对较弱,最容易出现伴随焦虑的创伤体验。(薛玉凤,2015)母亲的早逝使艾米丽在儿童发育期没有得到母亲应有的陪伴及照顾,而这个阶段恰是形成三观的重要时期,这对她的思维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母爱的缺失在艾米丽的内心创伤留下了潜在的种子。
著名创伤理论专家和治疗专家德瑞·劳和朱蒂斯·赫曼都认为,创伤不能独自面对,只有“在关系中”才有康复的可能。艾米丽既没有兄弟姐妹,亲戚也和家里闹翻,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缺乏陪伴和交流,成长环境显得压抑。艾米丽缺失“关系”,悲伤无人倾听,只能孤独地面对来自周围环境的种种压抑和束缚,致使其受到的潜在创伤无法愈合。虽然还有父亲,但他是南方父权社会的典型代表,其身上有着明显的南方贵族的传统特点——孤傲、专制和蛮横,是家庭的绝对权威。他告诫艾米丽要时刻维护格里尔生家族的尊严,因此在邻居的眼中她始终“把头抬得高高”,甚至堕落的时候也是如此,无法卸下贵族的面具。同时,父亲不让她与外界交往,“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背后, 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 背对艾米丽, 手执一根马鞭, 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而根据赫曼治疗创伤幸存者的经验,建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创伤复原的基础。[3](师彦灵,2001)父亲的行为再一次加深了艾米丽的心理创伤,使她的性格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逐渐改变。最后,在受到父亲去世这一创伤后,就好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艾米丽彻底崩溃了。
其次,艾米丽的创伤来源于爱情。“爱与被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Strout,2008)渴望被爱的艾米丽在忧郁压抑的环境中成长,在父亲去世的夏天遇到了精明能干的北方工人巴伦,她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男人,甚至放弃了她“淑女”身份。面对种种压力,她始终没有放弃,爱情让她又看到了希望,但这样的深恋却以巴伦不想结婚面临终止。这一次巨大的打击彻底摧毁了艾米丽对爱情和生活的最后一丝期待,最终坠入悲剧的深渊。
接着,艾米丽的创伤来源于当时的社会。“艾米丽的悲剧性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给予她机会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Ratna Asmarani,2017)艾米丽的悲惨一生看似是个别与偶然事件引发的表层创伤,实则投射出不可避免的悲惨结局的深层创伤,那就是南方人的集体文化创伤与清教主义的历史制度创伤。实际上,艾米丽是南方传统的牺牲品和殉葬者。当时美国内战摧毁了南方经济赖以生存的奴隶制度,随之而来的便是南方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彻底崩塌。战后,南方贵族彻底丧失了过去富足的生活,但他们仍然伪装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顽固地生活在自己幻想的尊贵的身份中,艾米丽的父亲便是其中一员。他将希望寄托在女儿的身上,艾米丽一生都顶着压力活着,被贴上贵族的标签,要活出高贵而顽强的形象,这样的标签使艾米丽困于牢笼中没有了自由,只能不断地被父亲支配。父亲去世后,早已被迫习惯于“高贵”的她依然保持着以前的举止,拒绝与别人交流,同时也不愿意纳税。这些举动都体现了南方战败之后给她带来难以磨灭的创伤。
而对于小镇上的人而言,从小生活在镇上的艾米丽是一种象征——对于新社会到来的拒绝。虽然艾米丽遇到了心上人巴伦,找到了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但是小镇上的人对于这段恋情的看法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有了一点寄托”,人们欣喜地看到孤傲的、高高在上的贵族小姐终于放下了架子,像普通人一样谈起了恋爱。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这种行为不应该是一名真正高贵的小姐所应做出的,是有损南方贵族尊严的,“格里尔生家族的人绝不会真正地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可怜的艾米丽活在了小镇人的视线中,一举一动备受人们关注。她被当作是小镇人维持南方传统的象征,是人们拒绝承认新社会到来的“最后一根稻草”。小镇上的人们不允许心中的里程碑倒下,无法接受艾米丽不顾及南方贵族传统与一个既无丰厚财产又无尊贵地位的北方工人谈恋爱。这些无不像张牙舞爪的魔鬼,紧追不舍地将艾米丽推向深渊。归根结底,当时的社会环境是艾米丽深层创伤的主要原因。
三
赫尔曼曾在《创伤与复原》中提出,创伤可以通过建立安全感、回顾和哀悼、重建与正常生活的联系来复原。父亲去世后,艾米丽失去了全部的依靠,但与此同时,她也脱离了父权的束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过自己的人生。实际上,她也逐渐意识到旧时代的没落, 开始下定决心改变,小心翼翼地向新文明迈出脚步:首先,艾米丽剪短了头发, 想要告别过去,“她病了好长一个时期。再见到她时,她的头发已经剪短,看上去象个姑娘”。其次,她学着勇敢,开始面对小镇居民,开始自己挣钱,通过开授陶瓷彩绘课教镇上的孩子来赚取生活收入,想要拥有经济支配的权力。最后,她试图追求爱情,在她心里,一份破天荒的爱情,或许就是对自己最后的救赎。艾米丽爱上了北方工头巴伦,一位贵族南方淑女与一位北方粗俗的野蛮人的爱情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艾米丽偏偏要这样做,这是她对新生的渴望,也是她对过去父权束缚的反抗。作为人群关注的焦点,她不再害怕别人的眼光,勇敢地同巴伦出游,放弃了贵族的骄傲和自尊,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大胆追求。但她并没有因此得到真正的救赎,她勇敢追求的爱情到头来只是泡影,燃起的对于爱情的向往和生活的希望再次熄灭,这也是艾米丽最后的创伤。
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创伤时代的艾米丽,注定是无法完成自我救赎的,治愈创伤的途径在于建立对环境的主控,这需要社会群体的帮助。但艾米丽所处的社会是冷漠的,镇上的人都看不起艾米丽一家,同时还带有异样的眼光。艾米丽在创伤下没有人安慰,无法建立安全感,失去了独立意识,因此治愈不了自己的创伤,改变不了自己,最终阻碍了她的救赎之路,不断地将她推向死亡的边缘。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通过对艾米丽的创伤症状描写,将南北战争后的旧南方传统、腐朽和残暴社会制度和文化对个体造成的创伤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作为作为没落的南方贵族,艾米丽由于困在父亲的强权和腐朽的南方传统制度文化的夹缝中,呈现出了孤独疏离的创伤症状;此外,艾米丽无法在冷漠无情的社会中建立安全感而掉入无尽的痛苦深渊中,最终只能孑然一身,孤独终老。艾米丽所遭受的创伤也暴露了南北战争之后,处于腐朽的文化制度下老南方人的缩影,虽然有过斗争,但是陈旧思想根深蒂固,个体的力量往往有限,结局只能以悲剧告终。
http://www.dxsbao.com/art/535208.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