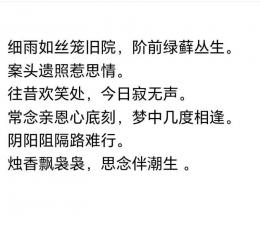“有妈真好,妈就是福呀!”这句话开始也没觉得有什么高奥之处,朋友散尽,晚上躺在床上,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泻进窗台。我是最喜欢在这样的时刻想点事情的,况且有乘着酒兴。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把什么都看透了,看淡了,虽然有些东西还看的不太懂——比如妈。说实话,很想写写关于妈的文章,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关于爸爸的文章我写过一篇叫《零星的记忆》,在《渔阳文艺》上发表了,是因为爸爸早已去逝,是因为爸爸那暴躁的脾气以及我与他的“恩怨情仇”,是因为他会那么多的手艺却最终也没能成为“匠”。妈太普通了,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看出来妈与众不同之处,但也许普通里面可能就蕴含着不普通吧,这是我在读林清玄《心的菩提》所感所悟。
每个人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或许三分之二的时间可能和爸妈生活在一起,不是吗?每次回家喊的第一声就是妈,“妈,我回来了。妈,您干啥呢?”那叫个自然。除了叫妈外,叫谁我都觉得不如叫妈亲切。有人说,妈在家在。妈在,老家叫家;妈不在,老家叫故乡,细细琢磨,这句话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妈在,就是期望,妈在,就是福分。逢年过节的,都要回老家看一看,回回家,看看妈,有一种心理和情感上的满足。
在北庄工作时,我每月都能回老家几次,那时回家顺路,觉得很方便。后来,调到了密云,我心想着每两周回老家一次,到后来想着每月回老家一次,但有时非心所愿,只能时不时的在电话里了解一下妈的近况。其实哪那么忙呀,连回家看妈的时间都没有?她现在岁数大了,一身的毛病,每天都得靠药顶着。还好自己能遛弯、能做饭。自己一人住在老屋里,虽然没伴,但也清闲。老屋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先前是青瓦石头墙,每逢阴天下雨时就成了妈妈的心病,山墙经常塌。后来我把墙体换成了砖墙,窗户也都换成了玻璃的,又做了保温。其实她没有必要一个人守着老屋,我们哥好几个,去哪家住不都可以呀,说了好几次,她硬是不同意,清闲过后是孤独,虽是这样,但她有她的想法,能自己动弹一天,决不给儿女找麻烦,老人们都这么想,也只好如她愿了。这种“如愿”我不知是她的无奈还是作为我们这代人的悲哀,最起码,我是这样觉得的。
妈现在岁数大了,腿脚更加的不便了,我告诉她,除了做点饭其他的什么事情也不要干了,妈听我的,但有一件事怎么说也不行。就是院子里每年到了应时的节令都要种上东西,主要就是棒子。先前,我家的院子比现在大,爸在世时,把院子打理的井井有条,这一点我在《小院》的文章中做过专门的描写。妈不会,妈说种棒子省事,好打理,要不种东西院子里竞长草。妈种棒子很简单,简单的就如同她本人一样。到了该种棒子时,就用镐在院子里不规则地刨上几十个坑,然后点子、浇水,这项任务就算完成了。等到棒子长到一定的高度,再在棒地里撒上一些豆角子。妈种的豆角有长豆角、秋豆角和扁豆角,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
我是个不善表达的人,妈也是,但每次我回老家看她时,我觉得她的话特别的多,她会把村子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告诉我。比如谁谁成了村书记,谁谁去逝了,谁媳妇和别人跑了,有时甚至把很小很小的事都告诉我。还说上次你回来忘了给你拿豆角了,园子里的豆角好吃的很,无污染。她还说,上次也忘了给你掰棒子了,这下都老了,回头碾成棒子米和棒子面拿上,省得买,好贵的,又不知打了啥药。我只有嗯嗯的份,但我知道,妈不糊涂,她最爱看中央三的节目,说起其中的明星来决不逊色年轻人。看到她那苍苍白发,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这种滋味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得到。我只能把这种滋味,写进我的文章里,渗透到我的心中了。
说实话,妈在年轻时身体可硬朗了,所以才能支撑起这个家。她一生共生了五个孩子,都是男孩,第二了孩子不知何原因没保住,剩下我们哥四个。说来也巧,老姨也生了四个孩子,但都是女孩。老姨想把我和老姨的老闰女换一下,不知是真是假,总觉这样就都好了,老姨有儿子了,妈也有闺女了,但妈没同意,她宁愿把我当闺女养着,所以什么苦活累活都不让我干,也源于我有三个哥哥做顶梁柱,所以我从小就受到优待。但不管如何,我觉得妈也不会把我过继出去的,她有一个心结,她虽没和我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但后来我也知道了她的过去。她在8岁时就被过继了出去,因为当时情况比较复杂,在这里就不细说了。虽然养父母(就是我后来的姥姥、姥爷)对妈不错,但毕竞这个家里还有七八个孩子,所以妈总觉心里有点不一样似的。小时候,我是最爱上姥姥家的,姥姥家虽然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大家庭,但相对来说特别的融洽。姥姥是个很大方的人,每次我去的时候,她都给我烙大饼吃,舅舅们只有看着的份,我小舅和我同龄,看到我吃烙饼,他气得把一碗滚烫的棒渣粥嘬个山响。每到这时,妈就白瞪我,并且说:“少吃点,给你小舅留点。”那时都小,也不明白咋回事,只知道姥姥家怎么这么多人呢,小舅舅也太小了,和我一般大,只觉得好玩。当我们走了的时候,姥姥还背着姥爷给我们拿咸鸭蛋。妈虽然不是姥姥亲生的,我觉得这一点妈最像姥姥了。那时,老姑已经出嫁了。老姑家很穷,三间土坯房,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什。老姑每次来我家,妈有啥就给吃啥,有啥就给她拿啥。妈常说:“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其实,小时候,家里生活状况不怎么好,那时每家都差不多。在上小学前,我都是穿哥哥们的旧衣服,那时也并不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等到了我上小学,说什么也不穿哥哥的下剩了,说实话,那时一是没钱,一是买什么都得要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买粮要粮票……直到后来我参加工作时才知那叫计划经济。想买点布做件衣服在当时就是一个奢想,可妈自有她的“招”。那时,村里根本就没有做什么买卖的,也不让做。但有一家除外,那家是专门卖旧衣服的。旧衣服我到现在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时可能也是为生产队创收吧。妈从旧衣服里挑了一身成色好的衣服,回到家中,把衣服洗干净,然后不知从哪又淘换点蓝色精,把旧衣服给染了一遍。当我穿上那身衣服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那身衣服虽然是旧的,染完后跟新的一样,那时衣服质量好,那一身我穿了好长时间。后来妈又从那家淘了几身衣服,同样染成了蓝色的,给几个哥哥穿。
六七十年代,正是热火朝天的年代。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平整土地。村北面河边在当时是河套,从上到下有几百亩的地方。当时大队长一声令下,用条石把河套边围起来,再用铁丝网把石块罩上,叫固定河床。然后把围起的几百亩河套划成四份,分给四个生产队。从山洼中取土填在河套中,这就叫围河造田。那时人们根本没有太多的想法,只知这一做法好,有了地就有了粮食,就不会挨饿了。那时队与队竞赛,组与组比拼。妈当时三十五六岁,又是妇女队长,觉得自己身体硬朗,所以干起活来比男人还卖力。妈开始梳的是长辫,觉得干活碍事,干脆剪了短发。脖子上围一块布,算是擦汗用的毛巾。从山洼到河套大概有两里路,那时没有别的运土工具,只有小推车,可想而知当时人们是何等的觉悟,硬是用小车填了几百亩的河套。妈当时饿了忍者,渴了就到河套边子喝点凉水。有时妈干一天活,工分挣的比男劳力都多,那时是按工分合算的。妈在50来岁时就安了牙套,妈说就是那时老着凉弄的,妈现在腰也不好,妈说也是在那时扭伤的。几年的围河造田,除了大队成为公社的先进外,再一就是确实收获了一季稻子。后来一场大水,把几百亩田地打回了原形,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伤痛。但不管怎么说,大队的出发点没有错,村人们忘我的干也是没错的,毕竞得靠干活来养家糊口,怪也只能怪水火无情吧!
后来,联产承包了,队里的田地、牲畜、家什什么的该分的都分了,该卖的都卖了,生产队也就没有存在的实际意义了。再后来,妈就不下地了,在家做做饭,养点鸡鸭什么的。再后来,爸爸去世了,妈就什么牲畜都不养了。这些年,就她一个人这么过着,一天天的默数着年轮,期盼着中华传统的节日。有时我在想,我都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妈还能默数几何?因为妈真的老了,她将会和村东头的槐树一样慢慢的老去……
http://www.dxsbao.com/art/14242.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