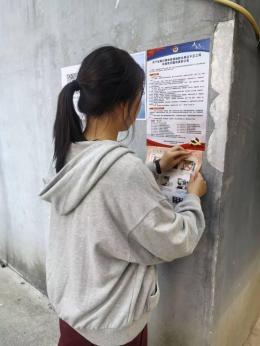湘江边的纤维丛
东方红广场的晨钟撞碎第六缕雾霭时,我正在数学楼顶层的文献室擦拭1957年的《数学学报》。泛黄纸页间滑落的俄文手稿上,陈传璋先生的批注墨迹未褪:“Петров-Крутенко映射在非紧流形上的延拓,当且仅当湘江水位超过36米。”落款日期是1975年涨水季,墨迹里还嵌着橘子洲头的红壤颗粒。
这是我大二暑假参与“湘江数学史整理计划”的第三个月。上周在复建的老红楼地下室,我发现了1982年数学系的油印讲义,空白处用红蓝双色标注着彭国甫校长手迹:“拓扑学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贝蒂数”。那些被白蚁蛀穿的章节里,夹着半片岳麓山枫叶,叶脉间用显微刻刀雕着莫尔斯不等式。
“小林,又在修复历史创伤?”学妹方棠抱着《代数拓扑习题集》探进头,她马尾辫上别的湘绣蝴蝶胸针,是用1998年校庆纪念章熔铸的。我举起沾着红壤的手稿:“看这个,陈传璋先生1957年的猜想,说湘江每次涨水都会冲刷出新的同调类。”
她突然按住我正在修复的纤维丛图示:“这个联络的曲率张量不对,应该用橘子洲大桥的悬链线参数化。”我们蜷缩在民国年间的铁皮档案柜间争论,直到老钟楼传来十二下青铜震颤——那是1953年从苏联运来的报时钟,钟摆上刻着华罗庚先生来访时的演算公式。
去年校庆日,我在数学系档案室撞见奇景。退休的彭教授带着研究生复原1980年代的拓扑学研讨会,黑板上的庞加莱猜想证明草图,竟与湘江防洪堤的等高线走向重合。当激光笔扫过某组同伦群时,突然有江鸥破窗而入,翅尖抖落的水珠在投影幕布上凝成庞加莱回归的轨迹。
毕业论文答辩前夜,我在附中老校舍发现锈蚀的保险柜。密码锁刻着陈传璋先生手书的“ε-δ”,转动时发出湘江夜潮般的轰鸣。当输入1982年《数学年刊》的卷号时,柜内跌出本泛着桐油味的笔记,扉页写着:“致我的κ,你在每条渐近线上都留下测地线的吻痕。”
书页间夹着半截粉笔,断面用显微针刻着非欧几何图形。在某条测地线的奇点旁,有人用红蜡笔写着:“所有未解的定理,都是橘子洲头未燃尽的烟花。”
答辩当天,我带着保险柜里的手稿走上讲台。当投影仪照亮1957年的草稿时,忽然有光斑沿着彭国甫校长的批注游走——那些被视作涂鸦的曲线,在晨光中显露出隐藏的凯莱图结构。当讲到庞加莱对偶定理时,后排的彭教授突然起立,他中山装第二颗纽扣的位置,别着1982年校庆特制的微分算子胸针。
毕业典礼那夜,方棠送我枚湘绣奖章。银丝线绣成的克莱因瓶表面,嵌着1957年的枫叶标本。当我们穿过桃子湖的垂柳时,她忽然说:“知道为什么选择陈类吗?因为它的示性数等于湘江大桥的车流密度在π时刻的期望值。”
此刻我站在橘子洲头,湘江水纹里漂浮着数学系学生最执着的偏导数。当游轮拉响汽笛时,我摸到奖章背面的刻痕,借着月光细看,是极小的楚文字——“Дифференциал несуществует, когда ты стоишь на мосту”(当你立于桥上,微分便不存在了)。
江风突然卷起1982年的油印讲义,那些被红蓝批注覆盖的公式,在暮色中显露出隐藏的纤维结构。对岸杜甫江阁的飞檐划过天际线时,我忽然明白彭教授常说的那句话:“记住,每个紧流形都是湘江防洪堤的局部投影,而所有洪水退去后留下的,都是代数拓扑最本真的胎记。”
http://www.dxsbao.com/art/726768.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