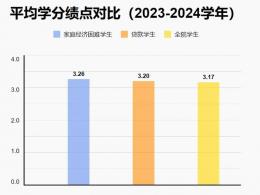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工进城务工,造成了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学生随父母进城随读导致的农村学校生源急剧下降的问题;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大,导致了乡村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能力和职业理念问题以及综合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学科教育和非学科教育)。
农民的温饱被解决,人们的需求层次便开始提高,“发展”成为了要务。“现在人生活水平也好了,不像以前,好像粮食都不够吃,现在都吃不完”。建国后,农民的身份地位不断提升,20年前,农民的地位逐渐下降,农村和农民不得不吃力追赶现代化发展的脚步。
农民若想摆脱身份束缚、以较少劳动换取更多收入,就需要从事非农业劳动。现在不少农民都认为“取得好学历,就能拥有好工作,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当非农业劳动成为地位上升和经济状况改善的重要途径时,教育便成为了实现身份跨越的门槛。农民以往难以获取到的教育资源,通过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现代教育。无数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出现后,农民们开始把希望寄托于教育:以最可靠的手段,教育成为了改变身份的捷径。就这样,农民被卷入教育洪流。大量的学生开始竞争,流入社会的劳动力也在增多。为了保证学生的就业,学历成为筛选劳动者的门槛。学历文凭成为村民眼中迈向美好生活的入场券:城市代表着富足美好,乡村代表着贫穷艰苦,乡村教育也随之变得应试化、边缘化,仿佛完成教育,就能逃离农村的苦海。按照这个逻辑,农村教育的功能就变得狭隘了,仅是利己主义的功利目的。
义务教育仅有九年,要想实现更高层次的突破,就不得不自费上高中、大学。一方面,教育资源和受教育人数的激增导致了文凭的“通货膨胀”,知识成为付费经济下的一种商品,教育成本陡然增高;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凭的贬值,农村的教育资源并未获得本质上的改善,“村里学生太少了,都去镇上上学了”,看似村小学逐渐被镇小学取代,但这一过程并未完成教育资源的整合和升级,村和镇的乡村教师彼此间流动、调动频繁,本质上是同一批老师,教学水平也是不分高下的。教育成本升高和教育质量较低的矛盾在农村变得尤为突出。这样以来,城乡教育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借助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农民家庭也只是少数,或是通过孩子自身的天赋,或是通过家庭的支持。
此外,人口流动也对农村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发展稳定的农民举家搬迁至城市,农村慢慢变得空心化,乡村教育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大坪村难以留住人才了。若不是自身喜欢乡下生活且有稳定经济来源,几乎没有青壮年劳动力愿意留在农村。一位在镇上开饭店的大坪村年轻夫妻说“我们是不喜欢、不想出去打工的那种,我们就喜欢在家里。因为农村的生活节奏慢…在农村哪怕今天买不起饭吃,我可以种田”。农村的就业岗位少、工资也较低,所以大多农民通过外出务工提高经济收入。
外出务工农民的文化程度和自身能力普遍偏低,加之大中小城镇存在的对进城农民的制度和文化排斥,导致他们在城市中无法接触到优质的工作资源,空间的位移无法为他们带来身份地位的流动,他们依然要靠大量体力劳动换取相对少量的收入。
当初代农民工发现仅靠外出无法得到与城里人相同的收入和资源时,便想到用知识实现地位的上升,从而实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所以目前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都受过一定的教育、是取得了高中及以上教育文凭的群体。这一群体有眼界和一定的经济实力,他们取得一定成就后,为了给下一代提供更优质的教育和社会资源,同时也为了方便照看,大多选择把孩子带至身边。这些能够走出去的孩子相较于留守孩子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农民身份和贫穷的代际传递;而留在农村由爷爷奶奶照看的孩子们只能接受农村教育,不少留守儿童还会因家长的忽视产生学习问题、生活问题。大坪村由留守儿童引发的问题有很多:厌学、脾气暴躁、抑郁以及生活难以自理,出现问题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双亲留守儿童,这些问题村民家庭很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孩子的问题(受自身能力和调研重点的局限,我们并未对这些家庭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大坪村妇联主任也在长期重点关注这群问题孩子,但未能很好解决这类问题。羊角塘镇的学生家庭于是出现了分化的现状:有经济条件和教育意识的家庭选择把孩子送至镇以上的地方读书,以求孩子能够走出农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外出务工,把孩子留守在家中由老人照看的家庭,会发现孩子的成长受教育资源的制约较大。
http://www.dxsbao.com/art/631190.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