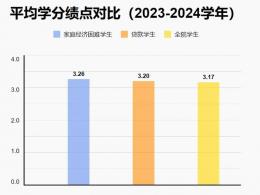四月二日,电影《我的姐姐》在全国上映,甫一上映,这部影片就引爆热搜,掀起了全国相当范围内的大讨论。
影片上映第四天,《我的姐姐》票房就破了四亿,成为清明档电影当之无愧的口碑、票房“双第一”。
影片中,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安然是一个独立、坚强的大学生,重男轻女的父母一直想要一个弟弟,为此,他们不惜让安然假装残疾以获得一个二胎名额。
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安然想去北京的高校学临床医学,却被父母偷偷改了志愿,只能就读本省大学的护理专业,父母给出的理由是:“女孩子早点毕业出来赚钱”。
后来,父母如愿以偿地生下了弟弟,但是一次意外车祸夺走了父母的生命,这让安然陷入了难题——是将弟弟送养追求自己的理想还是放弃理想抚养弟弟?
影片刻画了一位外冷内热的姐姐形象,本想丢下弟弟追求理想的安然,却被弟弟超乎年龄的“理想化懂事”所感动,两个人成为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电影名叫作《我的姐姐》,但实际上,这一短语背后的主体是弟弟。换句话说,故事的主角安然是女性,但影片却更多地站在男性的角度去讲述故事,《我的姐姐》更倾向于是弟弟的回忆录,是弟弟安子恒对姐姐故事的陈述,而剧中的安然和姑妈本身也是男性视角下的“姐姐”角色的具象展现。
有人说,《我的姐姐》是继《你好,李焕英》后的又一部女性家庭题材电影。但相较于真诚动人的《你好,李焕英》,《我的姐姐》评价却两极分化严重。一部分观众被姐姐和弟弟相互难以舍弃的亲情所感动,而另一部分观众为被家人道德绑架的姐姐打抱不平。
在这部打着女性题材幌子的男性视角电影里,女性角色俨然成了一个彻底的“奉献者”、“牺牲者”。
从电影本身的剧情来讲,《我的姐姐》以开放式结局来收尾,在最后一幕中,姐姐拉着弟弟跑出了寄养家庭。尽管和原生家庭抗争了这么多年,姐姐最终还是没有割舍下弟弟。这让影片前半部分展现的女性的强势形象被冲散,让观众十分恼火。
不难看出,影片中的安然虽然是一个独立女性的身份,但很多时候她都被贴上了“安子恒姐姐”的标签,从弟弟出生的那一刻起,安然就被强行安上了一个职责——照顾弟弟。
几乎身边所有人都认为她为弟弟的所有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姐姐安然成为了一个披着“独立”外衣的“被牺牲者”,所谓姐姐的独立和自由,似乎只是一个美妙却虚妄的泡沫。
为什么“姐姐”永远是牺牲者的身份?
追根溯源,还是离不开“姐姐”这个性别和称谓下所承担的社会压迫,而这,与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密切相关。
其实,早在古代,中国就是一个父系氏族,父权、夫权的统治长达千年,占据了几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所谓“男主外女主内”,便是说,在以往的观念下,女人要遵守“三从四德”,完全地服务于丈夫和家庭。到如今,男性的权威依旧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还有不少男性叫嚣着“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做家务等工作似乎成为了女性的天职。
同样是做家务,男人做家务会被评价为“好老公、好丈夫”,而女人做家务却被视为理所当然。一个不做家务的女人甚至会被唾弃为“不负责、没用的妻子”。这样根深蒂固的思想也使得女性的社会角色长期被禁锢在家庭范畴里。
现在,即便越来越多女性进入了公共领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和话语权,但她们仍是家庭最主要的照顾者,她们既要做到自己梦想的“独立”又被要求“做好份内的家务事”。
如此,女性在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反复横跳、精疲力尽,而大部分男性享受着性别红利,高高在上地坐在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上悠然自得,将家务等压力全然交给女性。
《我的姐姐》中已到中年的姑妈便是如此。作为姐姐,她不仅需要帮助弟弟照顾二胎,还为了弟弟放弃了原本触手可及的梦想。在姑妈长达几十年的“姐姐”生涯里,她习惯于付出、自我牺牲。在安然父母的葬礼上,姑妈忙前忙后,而男丁弟弟却在游手好闲地打牌。
男性凝视着女性,同时也在家庭领域剥削着女性。
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我的姐姐》是否烂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我们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扇窗,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千万女性在当今社会经历的不平等遭遇和在原生家庭受到的“精神迫害”。
影片中姐姐的困境也是东亚千万女性的困境,在这个被陈旧思想禁锢的社会下,她们被迫成为了“扶弟魔”。从我们身边那个叫做“招娣”的姑娘,到前些日子登上热搜的“现实版樊胜美”,不少女孩从出生前就经历了性别筛选,出生后更是被原生家庭强行与弟弟捆绑。
或许,“姐姐”们面对的敌人不是原生家庭,也不是弟弟,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人或物,而是一个千百年来延续的刻板传统,是早就渗入我们思想的亲情羁绊,这让女性在父系权威的天罗地网下苦苦挣扎、无处可逃。
这样一个广泛存在却甚少被讨论的话题,如今被搬上了大荧幕,让更多的人开始关心和思考女性议题,并对现状做出改变,这便是影片的社会价值之所在——问题意识比单纯的感官刺激更重要。
http://www.dxsbao.com/art/347848.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