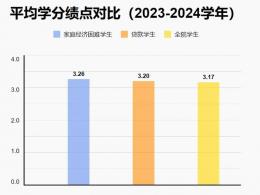2012年,70岁的莎朗·奥兹凭借诗集《雄鹿之跃》获得了当年的T·S·艾略特奖,次年又获得普利策诗歌奖,这使得她一时风头无两。然而,在那之前,尽管每部诗集都叫好叫座,但却总是入不了严肃批评家的法眼。
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作为今年上海书展的重要部分,邀请到很多国内外的重要诗人,但在这些诗人中,莎朗·奥兹却是最为耀眼的。尽管已经是74岁的老奶奶,但奥兹仍然优雅、迷人,充满活力。
在诗歌节期间,奥兹接受了东方早报的专访。就像她的诗歌一样,奥兹的叙述低缓、婉转,但却总能在云淡风轻中让人感受惊人的力量。
1942年11月19日,莎朗·奥兹出生在旧金山一个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家庭。奥兹的父亲是一个严格的教徒,但同时也是个酒鬼,酗酒后常常辱骂孩子。在奥兹的作品里,她经常提到的一个场景是父亲把她系在一把椅子上。对于这些,母亲因为无力或者恐惧,并不能给予孩子们什么帮助。
严格的宗教环境使得奥兹的童年充满了限制和约束:她不能看电影,也没办法获得像样的文学读物,除了像《奖赏》那样宣扬儿童为宗教殉道的教堂唱诗文本。
这种环境,并没有让奥兹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反而成为了一个“异端”和“泛神论主义者”,甚至用她自己的话说,“在15岁时,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直到60岁以后,她才能够确信并没有什么人笼罩在她的头上。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写出《撒旦说》《教皇的阴茎》这种“离经叛道”的诗歌了。
莎朗·奥兹比较正式地接触诗歌作品,大约是在小学6年级——她从压抑的家庭中挣脱,来到东部麻省的一所女子学校。在那里,奥兹阅读到了大量诗歌作品,其中最喜欢的是莎士比亚、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埃德娜·文森特·默蕾等人的诗作,但是只有艾伦·金斯堡的《嚎叫》被她放在包里带入了中学。
在过去评论家总是能注意到奥兹继承了惠特曼的诗歌传统,但却很少提及她在金斯堡身上获得的慰藉。实际上,《嚎叫》的意义不仅仅指向了奥兹令人窒息的家庭,同时还指向了她所处的美国“压制女性的时代”。根据奥兹译者远洋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妇女解放运动如暴风骤雨般撞进了奥兹的青春期。这不难与她后来的诗歌中的“大胆”、“出位”建立联系。
奥兹自觉进行诗歌创作,或者说诗人意识觉醒,则是在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进行“爱默生的韵律学”研究时,她发现了诗歌写作的秘密,由此开启了成为诗人的道路。八九年后,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撒旦说》(1980),随即就获得首届旧金山诗歌中心奖。此后,她的每本诗集几乎都能获得不俗的成绩。第二部诗集《生者和死者》,同时荣获1983年拉蒙特诗歌选集奖和美国国家书评奖。《父亲》入围艾略特诗歌奖,《未打扫的房间》进入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国家书评奖最终入选名单。
而真正使奥兹声名大噪的是2012年出版的诗集《雄鹿之跃》。这部讲述她遭遇丈夫背叛后离婚,以及离婚后自我解放的诗集,先后使她获得久负盛名的英国T·S·艾略特奖(2012)和普利策诗歌奖(2013)。在这部诗集里,尽管奥兹的经验是私密的——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离异,但是其中对于爱情、婚姻、悲伤、束缚以及救赎与解放的探讨,却使得她在诗句中,总能若隐若现地超脱私人经验,让个人情感上升为普遍情绪,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
虽然诗集销量不错,读者热捧,然而奥兹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身体与性爱,以及她浓重的叙事风格,使得批评家指责其“自恋”和“肤浅”。奥兹对此则安之若素,她告诉早报记者,“我想创造的艺术是大众都能欣赏的艺术,我不希望我写的东西太晦涩。”
但她也表示,在这个时代,很多美国人其实对诗人和诗歌也不怎么感兴趣,他们还是会以读得懂与不懂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
“但如果你在医院里服务,你有可能会见到不能说话甚至不能行动的病人,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写属于自己的诗歌。这时你就会明白,诗歌一定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它为人们的生活不停带来挑战和激励,这才是我真正重视的东西。”
【对话】
东方早报:你是如何开始进入诗歌创作的?
奥兹:有时候我觉得,早在出生之前,我就进入了诗歌。就像婴儿在出生之前就能够听到声音听到韵律,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你可以将这个视作开玩笑,但事实上我也部分相信这种说法,即人们早在出生之前就开始欣赏来自身体的音乐。我也从小就喜欢音乐,喜欢写作,喜欢绘画。
东方早报:你的第一本诗集叫《撒旦说》,是因为里面有首同名诗吧,后来编选集的时候,怎么没有收录进去呢?
奥兹:美国有个传统的儿童游戏叫做“西蒙说”——很多孩子在一起,其中的一个充当西蒙,发出指令,其他的孩子就要根据指令做出动作。这部诗集的名字就来源于此。之所以选择使用撒旦这个词,是因为我出生于一个宗教信仰十分严格的家庭,经常听到有关于天堂和地狱的事情。
当时把《撒旦说》这首诗放在这本诗集的第一首,因为我觉得用这首诗可以把这个世界颠倒过来。但是很多年以后,我在编选集的时候,会选择每一本诗集里面的精华部分,这首诗没有放进去,原因就是这首诗有一些脏话,会吸引太多的注意力。我不想让人把注意力放到这些东西上去。
东方早报:《撒旦说》出版于1980年,那时候你已经38岁了。在通常情况下来讲,这不算早。
奥兹:很好的问题。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很早就开始写作了,但是一开始,我写的东西并不好。于是我不断地练习、尝试。可能38岁时出版第一本诗集看起来有些老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正是一个合适的年纪。
东方早报:所以你想在做好准备,写作更成熟之后,再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是么?
奥兹:是的,这么说没错。看上去有些理想主义吧?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当时的作品也不足以被出版商所青睐。
东方早报:厚积薄发。
奥兹:哈哈,谢谢。但事实上,我自己的感受是,当我的作品最初被发表的时候,很多人都表示他们并不喜欢,有时候甚至还加上一些粗鲁的责骂。面对这些,我身体里坚强的一部分就不断告诉自己:他们只是还没有准备好去阅读你的作品,他们只是固执地认为你作为一个女人应该识大体、懂礼貌。
东方早报:结果一出版就得了奖,这对你继续写作来说会是一种鼓舞吧。
奥兹:当然。但在得奖之后,我依然能够收到对于我的作品的指责。所以一方面,第一本书就能获奖相当程度上激励了我;但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声音在对我说:你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你写的东西是不礼貌的。在面对这些指责的时候,我会说:噢,很抱歉,但这就是我呀。
东方早报:嗯,所以就像你之前说的,在写作中,你从不会因他人的评价而感到尴尬或者不自在。
奥兹:是的。我想创造的是大众都能欣赏的艺术,因此我不希望我写的东西太晦涩、太私密。我对写作的兴趣胜过了我对粗鲁指责的恐惧。
东方早报:所以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的每一本诗集几乎都能获奖,读者也很喜欢,但是批评家们却持续地对你做出负面的评价。
奥兹:我觉得人们想要的东西是不同的。有些人希望能够读到一些他们读得懂的、有关日常生活的诗,那么就我个人而言,我写的诗就是有关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然而另一些人呢,希望读一些聪明的诗、精致的诗、深奥的诗,(如果因此不喜欢我的作品)我觉得可以接受。
东方早报:我们对于美国社会、美国文化的一个印象是,人们对于平权看得很重。但是从你的经历中,似乎能够明显地看到,一些人对你女性的身份大做文章?
奥兹:是有这种可能。有些批评家本身就是女性,只是她们可能与我的想法不同。另外,在我的诗中我也用了很多诅咒的词汇,不好的词汇,这也是一个(招致批评的)问题。因为这些诅咒可能和宗教扯上了些关系,于是有些人就觉得受到了侮辱。另一方面,从传统上讲,女性是更不被允许以这种方式进行艺术创作的。
东方早报:在中国,“女诗人”这个群体的境遇很特殊,有时候,她们一方面被标签化、污名化,一方面“女诗人”的标签又可能为她们赢得关注——尽管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不够重视她们的文本。
奥兹:尽管美国和中国有很多不同之处,在这个问题上却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就我自己来说,我坚信如果我是一个男人的话,我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和尊重。但我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性诗人,诗人就是诗人。
东方早报:我发现你的诗歌中尽管非常多地描写性爱、身体,但似乎并不像中国一些下半身写作那样,以此为工具吸引读者眼球,你是如何让读者不过多被性爱、身体的描写吸引注意,并深入到其背后的意蕴去的?
奥兹:有意思的问题。每当我开始写一首诗的初稿时,我都会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除非我真正喜欢这首诗,并不断地花力气去改进它并把它寄给杂志,否则没有人会读到它。因此,在写作的时候,我感到充分的自由。
我还喜欢用圆珠笔在本子上手写的方式创作。在这个绝对的私密空间里我可以尝试任何我想尝试的东西。同时,我对“人”这个写作对象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希望在创作中保证精确,所以我会写那些,因为这就是我喜欢的、我的风格。
东方早报:中国人对诗人有两种想象。一种是理想化的诗人形象,高高在上,接近于神;另一种就和“疯子”“穷困潦倒”,甚至“神经病”相关。我想知道在美国文化中诗人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的?
奥兹:很多美国人对诗歌、诗人其实不感兴趣,他们对诗人的印象其实和你说的后一种差不多。而当他们听到一首诗的时候,会觉得“那也算是诗吗?为什么我不懂?”或者“这就是诗啊,我也能写”。
但如果你在医院里服务,有可能会见到不能说话甚至不能行动的病人,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写属于自己的诗。这样的场面,会让你感受到一种真正的鼓舞。我想说,诗歌一定是有它的价值和意义的。它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挑战和激励,这才是我真正重视的。相对而言,我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他人心中,就不那么重要了。
http://www.dxsbao.com/art/12235.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