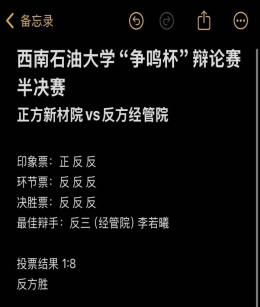当冬日的暖阳温柔地抚过青砖黛瓦,曲阜师范大学教师博物馆的飞檐斗拱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甲辰年腊月初一,“七秩师大路 情系曲园人”实践队的青年学子们,怀揣着对教育圣殿的朝圣之心,踏碎了庭院里凝结的晨霜。这座承载七秩春秋的时光圣殿,正以青石台阶为琴键,为后来者奏响穿越世纪的师道交响。
推开朱漆斑驳的棂星门,迎面而来的光影长廊宛如时光隧道。四百二十帧泛黄相片在楠木展墙上次第绽放,斑驳的光影交织成七十年岁月的长卷。首帧摄于癸巳年的黑白影像里,十三位布衣先生在断壁残垣间执卷而立,他们身后是临时搭建的茅棚学堂,檐角悬挂的铜铃在寒风中叮当作响。实践队长李墨的手指轻抚过玻璃展柜,惊觉相框边缘竟凝结着细小的冰晶——这分明是时光凝固的泪珠。
“当年我们备课的油灯,总要罩上三重宣纸,既防风,又能让光晕染得更温柔些。”徐明远教授沙哑的嗓音在穹顶下回旋。这位八旬老者驻足在1978级毕业照前,布满老年斑的手掌虚抚过故人的面容。他讲述起在煤油灯下编纂《论语新诠》的岁月时,穹顶藻井间忽然洒落一缕天光,为银发镀上金边,恍若当年秉烛夜读的年轻讲师穿越时空而来。
转角处的青铜戒尺在玻璃柜中流转着冷冽的辉光,戒面上“诲人不倦”的铭文已模糊难辨。一本1956年的备课本静静躺在侧,宣纸上的蝇头小楷工整如雕版,批注间的朱砂依然鲜艳欲滴。实践队员张晓雅俯身细看,突然轻呼出声——某页边角处洇染着深褐色的痕迹,讲解员低声解释:“这是当年刘文典教授咯血时留下的。”刹那间,整个展厅的空气仿佛凝固,只余下文物们无声的诉说。
拾级而上至典籍阁,樟木书架间浮动着若有若无的墨香。1937年油印的《国文讲义》扉页上,时任校长题写的“为往圣继绝学”六个大字力透纸背;1962年手抄的《教育学札记》里,红蓝双色批注如星斗般缀满页眉。当队员王清扬轻轻掀动《曲园七十年》的铜版纸页,几片干枯的银杏叶翩然飘落——不知是哪位前辈将秋日的私语悄悄夹藏。
暮色渐浓时,实践队员们驻足在观星台。远处大成殿的琉璃瓦流淌着晚霞的余晖,宛如先师们铺展的鎏金绸缎。徐教授从怀中取出半块残缺的砚台:“这是1958年洪水冲毁校舍时,老校长从淤泥里刨出来的。”斑驳的砚池里,依稀可见当年学子磨墨时留下的环形凹痕,如同年轮镌刻着不朽的师道传承。
风过杏林,带起檐角铜铃的叮咚清响。实践队员们将今日所见所闻化作笔尖的星火,在实践日志上郑重写下:“所谓师者,非独传道授业,实乃以心血为墨,以岁月为纸,书写民族精神的永恒诗行。”此刻,教师博物馆飞檐上的脊兽沐着新月清辉,仿佛七十年来无数教育者的精魂仍在守望,见证着新的薪火在这片圣土上生生不息。
http://www.dxsbao.com/shijian/720952.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