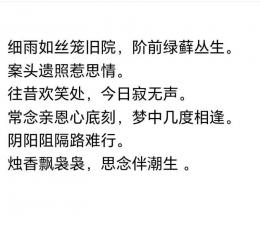放学的每个中午都如此相似,喧喧嚷嚷、吵吵闹闹。走了没几步,一个熟悉的身影跃入连心的眼帘。长长的脖子上顶了一个秃顶的脑袋,油腻腻的蓝色衬衫搭了一条明显偏长的黑色西装裤,脚上虽然蹬了一双闪亮的黑皮鞋,却更显滑稽。连心匆匆忙忙的走过去,涩涩的用蚊子般细弱的声音喊了声爸。连金伟没有回应。
连心熟练的跨上了那辆自行车,便赶忙低下了头,用两只手紧紧攥住车座的把手,不时地扭头看两边一眼。旁边的豪车的一辆接一辆的挨着,校门口的拥挤,让这些司机们恨不得给汽车安上两只翅膀。连金伟熟练地扭动着胖胖的身体,在车水马龙中见缝插针,并狂按着车把上的铃铛,遇见挡他路的人或车,还会叽叽咕咕的低声骂几句。十四五岁的年纪,虚荣心和自尊心早已长出、长大。连心每天都很害怕坐在豪车里的同学,探出脑袋向自行车后座上的她打招呼;害怕被爸爸骂的那些路人与爸爸真的在大街上对骂起来;害怕下午上学的时候同学问她带着你的那个是你爸爸吗。这样的忧虑让放学的这条路这么近却那么长。一丝自卑在连心的内心里渐渐晕开,放大。本无所羡,明妙坦荡,奈何生活不依不饶。初夏的阳光太刺眼,连心真的无法堂堂正正地抬着头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在一路的忐忑不安中,自行车终于驶出了学校门口的路。爸爸的叫骂声、铃铛声也渐渐停了。连金伟地压着嗓子说:“今天我们去医院一趟。”淡淡的口气,冷冷的。连心知道去医院是为了什么。医生宣布的三个月期限,想想也是到了。三个月前,医生二次开颅确诊了妈妈袁希的肿瘤为恶性,连心从姥姥绝望的眼神中,从舅舅的寂静无言中,从大姨快速利落地雇车将妈妈拉回医疗条件更差的老家的举动中明白了两个字—等死。 妈妈袁希被安置在阴冷的西屋中,连心去陪她,跟她说不了几句话。只是滚大的泪珠不断地从连心的眼里流下,用光了一卷又一卷的卫生纸。卫生纸皱皱缩缩地被堆在木桌的一角,却仿佛是整个屋里最有生机的一隅。癌细胞快速转移,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先是神智不清:妈妈会不停地问连心,她在哪里,会突然分不清好多人的名字,乱叫一通,会把原来的事情强加到现在。后来是不停地呕吐,将好不容易吃进去的饭一股脑的全倒出来,。那天村里有演出,不上课的连心去凑热闹,看装扮成女人的男人在舞台上搔首弄姿,看穿着戏服的年轻女子拖着长腔,甩着水袖发出凄婉哀转的声音。觉着无趣的连心买了串通红通红的糖葫芦一路小跑跑回了姥姥家,记得曾经这是妈妈的最爱。妈妈精神这天出其意料的好,吃下了整整一根。可是当连心还没来的及觉着开心的时候,呕的一声为前奏,接着血红的山楂皮,白白的果肉和发黄的胆汁一股脑的全被吐出来了。那一刻,连心跑了出去,不是因为恶心,而是因为痛,痛的她只能靠身体上的机械运动来缓解。在后来,癌细胞转移到眼睛,妈妈袁希在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依旧不停地问她,只是问题变成了:现在几点了,吐字也变得不甚清楚。连心对着那空洞的眼睛无助的哭,她跪在妈妈的床前,虔诚的祈祷神灵保佑她的妈妈,哪怕是一命换一命,自己死去。她竭尽全力的不让躺在床上已经瘦骨嶙峋的妈妈察觉,抽噎的声音被她生生地憋在喉咙里。可是母女连心,袁希格外镇定,云淡风清地说了一句:“还老哭吗?”
想到这里连心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全身的战栗让连心使劲收了收脖子。初夏的阳光这样的好,连心怎么这样的冷?
到了确诊妈妈病情的医院,这里曾经是痛苦的开始,想必也将成为痛苦的结束。如果真的能结束。到了四楼,向右转弯。连心看见了熟悉的不熟悉的,陌生的不陌生的人向她投来悲悯的眼光。不知是谁,将连心引入了一个病房。阳光尽洒的房间,遮掩了消毒水的味道以及生死离别的味道。连心很平静,静静地看着已经昏迷的袁希。那张已然找不出忧虑抑或焦急的脸庞。没有一声妈脱口而出。
一句爸爸说出的话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寂静。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午还得上学,却是连金伟带着连心回家,让连心错过陪着袁希走向生命终点的原因。一回头,已是此生缘分尽了,母女情断。哀莫大于心死,再见面,一个漂亮的人竟成了黑黑的冷冷的骨灰。
这天中午阿姨倍献殷勤,忙招呼着连心吃饭。,连心看了看那张脸,眼光下扫,最终落在那隆起的尖尖的肚子上,嘴角扯出一丝无奈的笑容。其实连心早已不在乎,何必藏着掖着瞒着她呢?机械地端起碗,匆匆扒了几口饭,悄悄扔下碗,逃进了自己的卧室。轻轻的关上房门,害怕一点声响惹出别人对自己的一番不满。随之,连心一下子瘫倒在地,伪装了太久,觉得心脏像充满气的气球,再拖延一会儿,定会炸的支离破碎。抱着膝盖,将头深深的埋进,任凭咸咸涩涩的味道流进嘴里,苦进心里。两只瘦黄的手用力揪扯着肥大的校服裤子,腿上感觉到一阵冰凉。明明夏天已经到了,她却像疾风里的树叶,颤抖哆嗦,无法控制。
六里外的市肿瘤医院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医生,从容不迫地摘下了手套,对着旁边年逾六十的老夫妇真诚无奈地说:“请节哀”。轻轻转身,渐渐远去,是无穷无尽的悲伤,汹涌而下却欲说还休。
http://www.dxsbao.com/art/76047.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