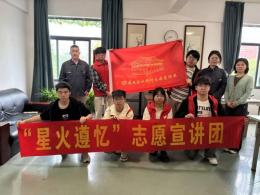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以男性作为支点,而张爱玲在其创作过程中,主角多为女性。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形象各异的女性,通过细腻而又悲凉的笔调对时代都市女性生活、心理等多个角度进行描写,铺陈浓重的命运悲剧性。在其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叙述中,探讨了女性为何陷入了生存困境。
在传统封建文化结构中,女性毫无主体性可言。为女为妻为母,一生生存在一系列男性庇护下的名份之中。除此以外,再无其他身份,更谈不上自我。在资本涌动与家族凋敝频繁的时代,女性作为置换物的属性更加明显。张爱玲笔下,那些几代同堂、看似兴旺的大家庭实则是是情感的荒漠,早早给女主人公种下了无爱的种子。女性是家族的多余者,身在其中,被忽视、被冷落,被利用、被盘剥。《金锁记》里曹大年夫妻为了攀上一门有利可图的亲戚并免去嫁妆,把妹妹嫁给了官宦人家的瘫痪少爷。《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生活在父母、兄嫂之中,却深感自己无亲可靠。哥哥在骗光她的财产后,反倒嫌弃她离异之人不吉利。《怨女》里银娣觉得“房间整个象只酱黄大水缸,装满了许久未换的冷水”,等等。血肉亲情建立在金钱利益之上,在这样压抑环境成长的女性,孤独与被遗弃是其最直接的感受。心灵如此荒芜与贫瘠,又怎能期望长出爱的花朵?长此以往,只会人性异化,长出恶的果实。
张笔下的女性总是互相争斗和算计,这个结果造成的原因和民国时代的女性处境息息相关,甚至这种处境在现代女性身上依旧存在。民国部分知识女性和男性一样读“先进的”的书,男性仍然是社会的掌权者,所以哪怕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很难给予她们与男性拥有平等竞争的就职机会。活在主流意识下的那些女性之间的“成功”,最后就变成比男人,男人成了女人向女人证明“成功”的一种依据,成了一种资源上的争夺,并无关情爱。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提到家道中落的小姐葛薇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不过是嫁给一个普通中产,谋一份稳定的工作。她条件尚可,奈何却没有向上的渠道,更何况是生活在更底层的女性们。《倾城之恋》中提到“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女性必须依靠男性才能得到地位与价值,在其笔下的爱情成了冒着浪漫泡沫的买卖。女性机遇与价值认同的凋敝,为“出走”打上了重重的疑问。
张爱玲冷静、客观、悲凉地审视着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的女性形象,她撕下了传统男性话语模式下给予女子纯洁、崇高的神秘面纱,对女性内心进行理性、批判的审视。张爱玲认为“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则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可见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复”,以男权为中心的外界社会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固然是女性卑下生存地位和不幸生活命运的重要原因,但其自身人性弱点也是阻碍女性解放自身的重要障碍。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小说对于女性劣根性批判的典型。作品一开始,葛薇龙初到姑妈家这么想着:“至于我,我既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若是中了邪,我怪谁去?可是我们到底是姑侄,她是被面子拘住了,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决不相信那些无聊的留言。”,她已然知道姑妈家鬼气森森,本该扭头就走,然而碍于面子,又高估了自己的自控力。心存侥幸,以为自己能满足欲望的同时逃脱代价,于是一去不返了。正式入住时,就被姑妈准备的衣柜迷了魂,“一夜也不曾阖眼,才阖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对姑妈为她安排的房间“心旷神怡”,“三个月的功夫,对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当姑妈以她为幌子吸引年轻男性时,葛薇龙从心有不愿到自我欺骗最后自甘堕落,烧完了自己的一炉香。从张爱玲冷静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葛薇龙坠落固然有姑妈的设计、乔琪乔的引诱,但其根本还是她无可挽救的虚荣心。
在当时社会中,女权运动兴起,影响颇大。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还是义无反顾地,自愿沦为男性的附庸。“念过两年书”的知识女性白流苏将成为范柳原的妻子变成谋生的唯一方式。曹七巧为获得“正头奶奶”的虚名和这份名份能给予她的财富,甘愿依附于自己厌恶的残疾丈夫,牺牲年青生命的正常情欲,心甘情愿带上黄金的枷锁,成为了一个旧社会的伥鬼。
张爱玲以女性切身的体验、细腻的洞察,通过万艳同悲的苍凉命运的描写,对其中的缘起进行清醒的认识与开掘,撇看父权文化层层伪善的表象,再现现实人生的真实状态,展示出女性解放的层层困境。深刻地提醒我们只有持之以恒自尊自爱自强自立,才能争取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http://www.dxsbao.com/art/656906.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