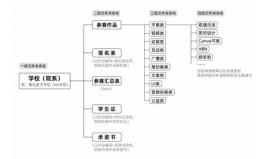在传统社会男女关系异化的情况下,女性被财产化,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改嫁再嫁的机会,女性的贞操被看作丈夫荣誉的一部分,所以更多是男性的一种扭曲癖好,此时男性话语的建构下的贞操却被冠冕堂皇地冠以美德的名号,钳制住女性的自由,其道德虚伪性显而易见。“道德这事,原是因为辅助我们生活而制定的,到了不必要或反于生活有害的时候,便应渐次废去,或者改正,倘若人间为道德而生存,我们便永久做道德的奴隶。”五四知识分子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对新式道德的追求成为他们摒弃旧式贞操观的动力之一,当贞操观阻碍了社会进步不具有积极意义时,自然不应当被称为道德。揭开其道德虚伪性的面纱后,五四进步者要建构起的是女性的自由,传统贞操观不只是对妇女婚前以及婚内性行为上有所要求,其严苛程度远甚于此,如“男女不杂座、不亲授”,男女有别的界限过于严格,这把女性深深禁锢在家庭之中难以进入社会活动之中,占人类群体一半的女性继续保持这般束缚的原状又怎谈社会变革?因此五四知识分子提倡女性的自由,一方面有恋爱自由,“贞操是因真正自由恋爱而结合的男女应遵守的规则”女性拥有追求恋爱的自由,贞操也不再是对女性的禁锢,而是双方真挚感情的一种纽带。赋予女性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同时,严格的男女有别约束也逐渐瓦解。二是离婚自由,“离婚自离婚,贞节自贞节; 贞节能否保持,并不在乎离婚不离婚。若一味不离婚就能保持贞节,何以不离婚而犯奸的,竟有如此之多呢?”,离婚再嫁和贞操丝毫无关,当夫妇相处拥有爱意时保持忠贞是合理的,但当感情破裂解除关系后贞操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于已无伴侣的寡妇而言,选择再嫁又或是仍保持对亡故另一半的情意不嫁,这更应由她自身的意愿决定,胡适说:“夫妇之间爱情深了,恩谊厚了,无论谁生谁死,无论生时死后,都不忍把这爱情移于别人,这便是贞操。夫妻之间若没有爱情恩意,即没有贞操可说。”胡适将贞操设定在婚姻内,但是也要有双方感情做支撑,这才算得上真正的贞操,只有婚姻之名无情感之实时贞操并不成立。
传统社会中的贞操观向来被看作是对夫妻间性关系的限定,童贞、妇贞、从一而终这三者都与女性的性行为挂钩,五四进步思想者对贞操观的这一批判经历了层层深入的过程,最终使贞操不再单纯依附于性行为,赋予了其精神特性。
首先,知识分子在维护贞操道德的基本立场上,率先主张铲除“童贞”和“从一之终”的贞操观念,《我所希望于男子者》写道:“中国的男子可以说是大半迷信处女的”,女子婚前有性行为就意味着失去贞操和名誉,五四知识分子将这种观点归结为处女迷信,认为对童贞做要求是对女性过高的道德约束,女性本该拥有自己的性权利。“从一而终”则酿就了大量节烈妇女的悲剧,剥夺了妇女的生命和价值,应当彻底摒弃。基于对童贞和从一而终的批判,他们把新贞操观限定在婚姻之内,即并无解除“妇贞”,只是增添了男女平等,“贞操是附带于结婚的,结婚如果丢开贞操不讲,那结婚就无意义了”,一些人将贞操看作婚姻之所以可能的依据,将贞操只与婚姻挂钩,但现实中难免会出现夫妻不和离婚的现象,这样就能说他们因离婚双方失贞了吗?这显然与他们所提倡的离婚再嫁不失贞操观点相悖。
于是知识分子不再一味地将贞操局限在婚姻内部以及单纯与性行为相关联,贞操更多是在两人真诚的爱之上的性关系,无论男女都要在爱情的基础上与对方发生性行为,提倡灵肉一致,“恋爱与贞操是有机的结合,恋爱绝无贞操的保护,则恋爱成了淫荡和浪漫;贞操而无恋爱的基础,则贞操成为性的强迫占有和对女子所加的野蛮束缚,成为奴隶的道德。”这种转变规避了离婚自由和贞操之间的矛盾,也保留了贞操的道德性,只是这道德性与爱情相联系,要求男女任何一方都要对爱情保持尊重和忠诚,“我不以为处女为可贵,我以为‘忠实’是要的,所以谈‘贞’不如谈‘操’,谈‘贞操’不如谈‘忠实’”,相对宽松自由的恋爱贞操观客观上也为个人追求恋爱自由和人生幸福创设了条件。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胆发声,对封建贞操观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一方面,他们高举女性自由、男女平等的大旗力图推翻封建贞操观,指出封建贞操观充斥着虚伪的道德感,它既是对女性的压迫禁锢,也是对人性的扭曲,女性作为“人”理应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性权利和婚姻自由,这一点在当今看似正常不过,但在当时封建贞操观的强大势力下,能够呐喊出女性也应当回到“人”的状态是一种思想上的极大颠覆。另一方面,打倒一面旗帜还要举起一面新的旗帜,来引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五四进步者大力构建新的贞操观,翻译日本有关女性主义的著作并吸纳其中进步观念,从提倡夫妻婚姻内互守贞节到扩展到恋爱贞操,贞操更是双方对爱情保持忠诚的精神坚守,这顺应了当时青年男女重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趋势,保障了女性的性权利,其中的主要思想也流传至今为我们当代人所认可,对构建合理的恋爱和婚姻观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
http://www.dxsbao.com/art/629938.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